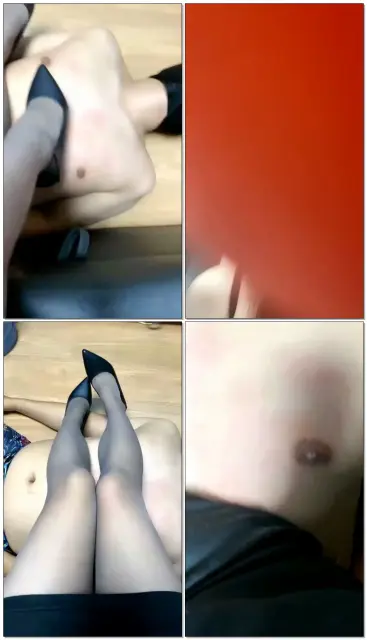追忆足控年华
2,899
女孩。午后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将她的童真揉作光晕。很可爱的女孩,让我想到小兔子。她穿着白色连衣裙,童装的,毫无曲线。一双粉色的露趾凉鞋。
我不认识她,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当目光掠过她小小的,素裸的脚趾,我忍不住地幻想她的人生。多么漂亮的小脚啊,假以时日,趾骨会变得修长,趾甲会带着各种色彩,足跟会变得饱满,如同她的身材一样。她会喜欢被男人爱抚双足?她的双脚会被捧入口中吗?或者,她会享受被戴上项圈,被竹签鞭打足弓吗?孩子总是充满了可能,时间带着成长的面具,将可能一一抹去。
幼时的我在姐姐的房间,第一次触摸到指甲油。那时的我还小,不知道不止双手,双足也可以抹上色彩。那是白色的小小一瓶,我扭开盖子,盖子连接着一个更小的刷子。我拿起沾染着粘稠白色液体的小毛刷,涂染我的食指。
我的精液第一次沾染上女人的脚趾,又是何时呢?是那时候的女友吧,我握住她的双脚,用她细腻的足弓揉蹭我的阴茎,柔软,温热,精液就这样喷涌在她涂着淡紫色甲油的双足上。其实她并不乐意,在我不断地哀求下,才勉强同意。我们的关系也并未持续很久。唉,恋足癖的男人就是这样,中意的是脚,不是人;总是将女人当做她们美妙双足的附属品,无法拥抱她们的人格,无法从她们身上得到归属感。永远都会有更美的双足,永远都会有想要品味的美好,永远在片刻的欢愉之后,就立即陷入虚无。如果没有恋足癖,我能否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呢?我也不知道。
小女孩快要从我肩旁走过了。多么可爱的女孩,眼睛尤为动人,带着未被污染的美好。让我想到童年,想到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以及随之失去的一切可能。但在恋童者眼中,她是欲望之火。
每个人都是符号,每个人诠释符号。就像对我而言,双足是色情的象征,但对医生们而言,却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人体部位。我对女孩没有欲望,即使看到她们漂亮的双足,幻想的也是那双美足的成长,并非当下。但在亨伯特们看来,她们就是当下的美好,而成长,就是死亡。每个人都自顾自地解读符号,基于认知,基于过往,没有相同的人,自然也没有相同的符号。
我没有童年的创伤,也没有复杂的过往。我将女人的双足认作美的符号,是与生俱来的。我很清晰地记得,我从小就对女鞋格外注意,每当穿着细跟高跟鞋的女士从我身边走过,鞋跟叩击地面发出清脆声响,我的心都会微微颤抖。那时我对性还一无所知,就是单纯地迷恋女人步伐的声响,喜欢高跟鞋的模样,以及鞋跟和鞋底所构成的美妙负空间(Negative Space)。
童年时,我家有订阅时尚芭莎,中国版的。时尚芭莎的封面通常是女模特,女明星们穿着各类衣装,各类鞋子,化着各类的妆,摆出各类的姿势。但吸引我翻开杂志的,并不是那些女人的脸庞或身材,而是她们穿着的鞋子,以及隐于其下的双脚。我不敢光明正大地看那一本本的杂志,总是在妈妈不在家时偷偷翻看,我不想被妈妈认为是性早熟。除此之外,小小的我隐约地觉得,喜欢女人的双脚是一件比性早熟还更难堪的事情。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已将女人的足部等同于性,超越于性。
在翻阅中,我对女鞋有了更多的认识,平跟鞋,长靴,乐福鞋,以及那双让我在合上杂志后,仍萦绕在脑海,不肯散去的露趾凉鞋。一个深色头发的白人女模特坐在藤椅上,穿着白色的宽松裙子,微微抬腿,一双木色的露趾凉鞋交缠于她的双脚,脚踝部分也带着镂空的编织,向上延伸至跟腱;她的脚趾被涂上了裸色的甲油,是非常微妙的裸色。那个下午,我就这样看着她露出的脚趾,想象着她并未露出的前足掌和足跟的模样,我忘了时间,忘了周遭,不愿离开目光。我仿佛是奥林匹斯的一缕春风,陪伴阿芙洛狄特漫步溪边,她穿着希腊的凉鞋,毫无掩饰地展现自己的美,淘气的溪水跳脱而出,沾湿了她美好的趾间,而她,止一笑而已。
我的阴茎无可避免地充血了,这是记忆中我第一次因为女人的双足而勃起。我多么想要触碰那双美足,抚摸那精致的脚背,再慢慢将凉鞋解下,让赤裸的足弓贴向我的脸颊。是的,我的愿望仅此而已,年幼的我从未想过要那双美足包裹我的阴茎,再用精液将其标记。年幼的男孩不谙世事,因而并不污秽,只是单纯地想要体会那一份美好,和女孩儿想将星星捧在手心的愿望并无二致。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蠢得足够天真,也就不会有迷茫;随着成长,随着认知的增长,人类却无法摆脱迷惑,反倒陷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漩涡。
步行街上熙熙攘攘,我看着无数男人和女人迈着脚步,穿着不同的鞋子,带着相异的表情,前往各自的目标。我想,也许每个人的命运在精子遇上卵子的那一刻,就已被决定了。就像我的恋足癖一样,也已被早早定下。那张时尚芭莎上的美妙影像,的确是我足控的启蒙,但也仅此而已了。即使我没有看到它,也会另一双美足将我启发;不经由杂志,也会经由书籍,电脑,电视。根本的成因在于我自身,只要我还是我,便无法舍弃对女人双足的爱恋。
我也曾想如平常人一般,爱上某一个女孩,牵着她的手,慢慢老去。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了,这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若一个女人没有一双足够触动我的双足,我便无法爱上她,即便她爱我,即便我们的观念是如此相合。我固执地认为,女人没有美足,如同金丝雀失去色彩,又怎么会美呢?既然没有美,我又怎么爱得上呢?而那些拥有美足的女子,即使我与她们达成了关系,却也很快就分崩离析。也许因为我极度的恋足行为,让她们无法忍受,也许因为我在拥有她们的同时,却仍觊觎其他女人的双足,让她们感觉到了背叛,也许因为我总想着将自己喜欢的色彩和鞋子强加于她们,是的,我喜欢这样,通过这样,我感觉到了美的创造。总而言之,我没有爱情,也体会不到爱情,我有的只是对美足的追寻。对美的追寻。
我开始找妓女。用钱雇佣她们的双足。妓女不会抱怨,对穿上我带来的鞋子这一条件也并不抗拒,换涂趾甲油一事倒是有些麻烦,但若给的钱足够,她们也会照做。
我的第一个妓女是由同好介绍的。他告诉我,她提供足类服务。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在酒店的房间等待,很快,门敲响了。她的脸算不上很漂亮,但即使隔着衣物,我依旧能看出她有着极佳的骨骼比例。她化着韩国式的流行妆容,穿着黑色T恤和抹茶色的瑜伽裤,配一双亚瑟士跑鞋。看着并不像一个风尘女子。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这样方便些,她说。
方便些?
警察,还有好事的人。她这样回答。我没有多问了。
她当着我的面脱去了外衣,毫无羞涩,只剩棉袜,内裤和乳罩。已经洗浴过的穿着浴袍的我,就这样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将最后脱下的袜子和其他衣物一并收拾好,放在一旁。她的内衣是成套的白色,她的脚趾涂着枫叶红的甲油,我对这样的红并不排斥,但也谈不上多喜欢。
你能穿上我带的鞋子吗?我问。
可以的。她说。
我从茶几上的鞋盒中取出一双黑色女用皮鞋,37码,是奇洛(Clarks)产的,皮质优良,有着10厘米的方跟,鞋头是较为缓和的尖头,短短的鞋舌上有着三个淡金色的金属链,有点像橄榄。我在购物中心看到了这双鞋,觉得好看,摸了摸,手感也好,我便买下了。这双鞋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是特意为某个妓女准备的。我总是购买各种女鞋,网购也好,实体店也罢,买下来之后就放在住处的储物室,时不时拿出来观赏一番。以下为收费内容(by http://www.prretyfoot.com) 我拿着鞋,半跪在地上,她伸出脚,待我为她穿上。她的脚趾很修长,尤其是第二趾骨,尤为美妙。不足之处在于脚掌,有些过窄了。我托着她的足弓,将她的脚护入鞋中,左脚,右脚,两只都穿上了。我不知怎的,我为妓女穿鞋,让我想到了拜占庭贵族为表臣服,亲吻皇后狄奥多拉脚背的场景。
能走几步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在酒店房间铺着地毯的地上,走了几步。
在妓女背对我的瞬间,看着她交替摆动的双腿,我感到了失望。我为何会失望,是因为对我而言她不够漂亮吗?是因为她的双足不称我的心意吗?是因为她的步态不够美吗?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失望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如何消解。直到两年之后,我遇到林小姐之后,才找到答案。
但既然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也不想浪费钱和时间。那天夜晚,我带着期盼来到酒店的房间,不愿空足而归。
我让妓女在床边坐下,伸出右脚,我缓缓将她脚上的皮鞋褪下,我握着她的足心,将她的脚掌置于鼻尖。我贪婪地品嗅她双足的气息,将女人足部特有的混合了体味、沐浴露、香水、皮革还有汗味的复杂气息尽数吸入鼻腔。我将她的拇趾含入口中,尽力地吸吮,如同婴儿吸吮母亲的乳头一样。我为她的足底抹上润滑液,让她用足弓握住我早已肿胀的阴茎,夹裹,磨蹭。
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很配合,也没有任何表示反对的话语。即使我将精液喷涌在她白皙的脚背,流入她的趾缝之后,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在询问我是否结束了之后,便到浴室清洗了。
她很职业,妓女都很职业。她们大抵都有着美观的双足,精心呵护,总带着不同的色彩。妓女和顾客在开始的时候不需要有感情,在结束的时候也没有牵绊。妓女会配合我的需求,也不会对我的恋足癖感到排斥,她们见过更奇怪的客人了。除此之外,在品味她们的双足之后,只要我没有意愿,我们就不必再联系,她们自然也不会在意我对下一双美足的追寻。妓女的双足能让我得到美的感受,能满足我此前在普通女人那儿得不到的需求,即使这种满足是一个漏水的碗,带着无法填补的缺口。
我始终无法感到满意,总觉得缺少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在妓女那儿得不到的东西。不是爱情,我不需要爱情,也不是因为她们的双足还不够美,我在那之后还找过很多妓女,她们其中的一些有着无与伦比的曼妙的双脚,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在步行街上,我继续行走,阳光为行人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一个穿着墨绿色长裙的女人,从左前方迎面朝我走来,我注意到了她的鞋子,一双介于黑色和深蓝之间的尖头高跟鞋,不露趾,大概是麂皮做的。黑色丝袜将她的小腿包裹,在太阳的辉煌下泛起白芒。
在我生活的世界,高跟鞋和丝袜已经成为了符号,也许象征着性,也许象征着美,也许象征着物质主义。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它们象征着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我”,“我”认为它们象征着什么,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在遇见林小姐之前,我一直都这样想。
我执拗地认为,只需由我赋予符号意义即可,只需由我妆点女人的双足,将它们变成我所渴望的美,再由我最终品味,一切都只需由我完成。我用分离器将她们的脚趾隔开,拿着小小的刷子给予它们不同的色彩,为她们穿上好看的鞋子,让它们成为我喜爱的模样,一切都取决于我,也只需由我来定义她们的美。我以为每次将精液射在女人双足后所感到的失望与虚无,都是生命的必然,都是解不开的戈尔狄俄斯之结。遇见林小姐之前,我就是这样想的。
她姓林,但平时我只是以简单的“你”与她交谈。而在我无意识的思绪漫步时,却总将她呼作‘林小姐’。她让我想到林黛玉,并不因为她的娇柔或是眼泪,而是她自觉的美。自我认可的美。
我是在露天泳池遇到的她。我常去露天泳池,并不是因为那儿女人赤裸着的双足,只是因为我喜欢游泳,喜欢春日的微光闪烁于水面,喜欢光线透过池水触及皮肤的别样温暖,这让我感受到了属于这个世界的,不容辩驳的美。也许命运就是如此难以解释,恰是我的无意带来了答案。
一个平常的周六清晨,阳光也寻常的明媚,登出泳池扶梯的我,见到了林小姐。她穿着深蓝的连体泳衣,躺在池边的沙滩椅上,她头发微湿,戴着金属框的墨镜,头倾斜着,似睡非睡,一条浴巾横覆上身。最先让我注意到的,是她的双手。她的前臂搭落在沙滩椅的扶手,手指垂下,指甲上涂着黑色的釉质甲油,非常显眼。她的手很好看,指节细长,褶皱也少,点缀在她指尖的黑色更是美妙,让我想到大马士革。她的双足会是怎样的呢?也如双手般美丽吗?带着这样的好奇,我望向她露出浴巾的双足。
她的双足赤裸着,不大,大概是34码,不会超过35,趾甲上也涂着同样的黑色甲油,趾节美观,最易露怯的小趾也很好看,脚掌的宽窄恰到好处,唯一可挑剔的是脚背,也许再高一些,会更具美感。她的双足美丽吗?我自然觉得是美丽的,但让我在意的并不是她的双足,是她的姿态。
她是放松的,却也是刻意的。她的左腿屈膝,脚掌撑着沙滩椅的坐面,右腿伸直了,右脚越出了沙滩椅,扮似无意地垂吊,在空中。
太阳照耀,轻轻波动的池水如金沙起舞,阳光的柔纱拂过她的双足,降下神谕般的洁白,碎石地板没有忘记她右脚的影子,就像我没有忘记那天她带来的刻意的梦。
我此前并不认识她,甚至连她墨镜下的双眼也未曾见到。但在那一刻,我坚信,她在展示自己的美。不是肌肤、乳房,或是腰部的美,是且只是她双足的美。阳光是她的镜子,她是池边的纳西瑟斯。
水珠从我身上滑落,春日和煦的风略过站在原地的我,仿佛将我带回了童年那个忘神的下午。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所寻求的能够填上那漏水的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美在自我认可时,才正真完整。她认可自己的双足,毫无掩饰地展现自己的美,有或没有观众,她并不在意,她的自我才是关键。于是,美被完成了。
我站得太久了,目光也太长时间未曾移动。她注意到我了。她转动脖颈,躺得正了些,即使隔着墨镜,我也清楚她的眼睛正注视着我。我没有躲避她的目光,同样看向她,很快,我看到她的嘴唇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动。我不需要多想,径直走向了她。
“你的脚很好看。”
她摘下了墨镜,我看到了她的眼睛,她的脸。她没有化妆,没戴美瞳,眉毛也只是简单修剪,没有纹过的痕迹。我对女人的脸并不那么看重,也说不好脸庞的美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但我想,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讲,素颜的她应该被归于好看的那一边。
她没有因我的话语而显出任何的诧异,也没有起身,她将手中的墨镜折好,放入一旁的防水包,揭开浴巾,披于肩上。
“你是第一个,第一个真的说出来的人。”她说。
太阳隐没于云层之中,它的金纱也随之从行人的身上离去,我继续行走在街上。林小姐在我身旁。我思絮飘来飘去的这个下午,她一直都在,她的左手牵着我的右手,与我一起在街上闲逛。她的手心温热,指甲触及我的手背。
我和她交往了,连父母都见过了。从客观视角来看,我和林小姐只不过是又一对平常的男女朋友,有些时候甚至连我都这样想,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此刻的她穿着卡其色的宽大工装裤,和一双彪马的麂皮浅蓝休闲鞋,没有露出她的小腿和脚踝,她的漂亮双足也被遮盖住了,就像我和她的关系一样。
我和她会像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一样亲吻,一样做爱,一样在秋日的午后双双卧在郊野公园的草坪,期待松鼠来到身旁。我有时忍不住问她,这算不算是一种刻奇(Kitsch)呢?她反问我是否讨厌这样,我说不讨厌。那就无所谓是否刻奇了,她说。
在认识她之前,我并不知道‘刻奇’这个词的来源,或是其背后的含义,是她告诉我的。
“是德语,K-i-t-s-c-h,大概可以翻译成自媚吧,昆德拉的小说经常用这个概念。”那天在她的卧室,她一边俯身涂染趾甲,一边这样对我说。
“不太明白。”我说。
“比如说,你为亲情感动,然后又觉得能够为亲情而感动,实在太好了。前者和后者都是刻奇,不过后者程度更重。”
“等一等,猪头过载了。”
“我大学的室友会夸我的脚好看,我之前告诉过你,对吧?她确实会称赞,但我知道她之所以这样,只不过因为她认为称赞别人是一种美德,才会去实践这种想法。这也是刻奇。”她已经涂好了,正在将泡沫分离器逐个摘下。
“现在懂了。”
“帮我把光疗灯拿来,那里。”
我把美甲烘干机从木架上拿下,递给她。在她把脚置于那蓝色的LED灯下,等待油和胶凝固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对女人美足的渴望,是否也是刻奇呢?
我追寻美足,无疑是为了迎合自己,我就是喜欢女人的双足,天生就是这样。但我并没有对我的行为感到优越,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审美高于别人。正如我之前所说,每个人看待符号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寻,我从不批判任何人,我也只是想追寻自己所爱的事物而已。
她的顾足自怜又是否刻奇呢?她明确告诉过我,她知道自己双脚的美,她也经常换涂各色的甲油,驳上各类的甲贴,再穿上凉鞋或人字拖,行走在月光下,低下头,自顾自地盯着自己的步伐,欣赏自己的脚趾以及新鲜的颜色。她喜欢这样,毫无疑问,也肯定是为了迎合她自己。但是除此之外,她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她看书,她粉韩国明星,常和女伴们去电影院,也喜欢漂亮衣服。她说,她也一直认为双足是性符号,但她不恋别人的足,只恋自己的罢了。
“搞定了。”她的话将我从乱流中抽出。“怎么样,你觉得好看吗?”她问。
回过神的我望向她的双足,趾甲被涂上了裸粉色,像樱花,还有些像冷藏过的金枪鱼腹,右脚中趾戴着一个银色的趾戒。
“好看,很合你的肤色。”
“喜欢吗?”
“挺喜欢。”
“让你想到什么了?”
“金枪鱼大腹。”
“哈哈哈哈,写首诗送给我呗。”她咧着嘴,笑个不停。
我很想写一首短诗赞美她的双脚,但大脑却不配合,皱眉想了半晌,也作不出半点词句。
“写不出来,还在想刻奇的事。”
“哎呀,别想了,说到底这不过是概念罢了。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只要不是专制的刻奇,就无所谓了。”
我迷糊地点了点头。
“放心吧,你也许是最不专制的那个了,我知道的。”她又笑了笑,“不然我也不会和你一起了。”
“是这样啊。”我说。
“过来。”
“怎么了?”
“你不想试试吗?”她说。
她坐在床边,微微伸腿,我盘腿坐在木地板上,身子前倾,接过她的双足。我的掌心托着她的足弓,抬至眼前。
她的皮肤是暖性的,偏白,脚背和足弓内侧的血管并不明显。我觉得相较银色,铜色或金色的趾戒会更适合她。但我从不要求她迎合我的审美,我就是想要看到她自我的表达。这又算不算是一种专制呢?我也不知道。
我的鼻尖贴近她的趾尖。她还没洗澡,足尖还残留着她穿的高跟鞋所留下的皮革气息,以及一丝汗味。我轻吻她的脚背,然后是拇趾,我抬头看她,她双臂撑着床垫,也看着我。
我将她的拇趾含入口中,吸吮。我的门齿轻轻磕碰到了她粉色的趾甲,伴随着她细腻的足肤,一丝咸味也略过我的舌蕾。我握住她右脚的足跟,亲吻她的足弓,再将其端起,贴向我的脸颊。我闭上眼睛,枕在她的脚上,脸上也许带着笑容。
“在想什么呢?”她问。
“西比拉和贝里昂,耶路撒冷的夏夜。”
“啊,大概能懂。”她说,“脱下裤子吧,男爵。”
我站起身,脱下裤子。我的阴茎早已充血了,她的双足握住我的阴茎,双腿轻轻浮动,足心揉搓着我。她的足肤足够细滑,无需润滑液的辅助。
她脖颈微斜,上身半卧在床上,短裤已退至根部,双腿内侧的长收肌紧绷着,连接小腿,操纵双脚,为我足交。
她是那么的美,又是那么的毫不掩饰,我毫无抵抗之力。
“要射了。”我说。
“还不能射,”她停下了,脱去短裤,内裤,然后是上衣,乳罩,全裸地躺在床上。“但你可以射进来。”她说。
“好。”我说。
相比她的阴穴,我更想射在她的脚上,但如果这是她的想法,她的愿望,那我也愿意照做,她若欢喜,我又怎会难过。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爱情,但我的确不讨厌这样。
我们走得有些累了,便在街边的一家轻餐厅坐下了。我们坐在露天的餐桌边,桌子和椅子都是木质的,一把巨大的沙滩伞覆盖着我们。
我望着街上的行人,有孩子,有情侣,有夫妻,也有落单的人。我和她的关系到底属于哪种呢?是伯牙子期吗?是情侣吗?是朋友?或者只是性癖相同的人,就像那些SM关系的女人和男人一样?
“又在想些什么呢?”她望向我,问道。她今天化了淡妆,没涂口红,也没画腮红,热烈的阳光倒是不愿无为而无不为,将她的面颊烤得微微泛红,仿若天然的胭脂。
“在想我们的关系。”
“怎么了呢?”
“我们最初像池水和纳西瑟斯,像是镜子,现在却有些像丘比特和赛姬,像普通的一对。我还想,前者和后者,哪一个更刻奇呢?但想啊想,却想不出来。”
她也想了想,然后握住了我的手。她今天换涂了淡紫色的指甲油,有些像桔梗花。
“哎呀,早知道不告诉你‘刻奇’这个词了,现在住在你的脑子里,走不掉了。我觉得说到底刻奇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概念,就像很多其他没用的东西一样,人类摆脱不了刻奇,再怎么想也没用。”
“也是。”
“而我们的关系,当然可以是纳西瑟斯和池水,之前是,现在也是啊。只不过,也不需要非得像纳西瑟斯那样疯吧?我和你在一起,也并不只是因为你能迎合我的自恋,也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有趣,很亚撒西,不是那种直男式的温柔,是那种恋物癖男人特有的态度,你能明白吧?要我说,纳西瑟斯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刻奇精。哪有什么无尽的追求啊,活在当下,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就好了。”
我点点头,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
“你和我一起,开心吗?”她问。
“开心啊。”
“那就行了呀。”她笑了笑。
这时,服务员拿着菜单,来到了桌边。
“请问两位想点些什么?”
我抬起头,看见太阳在远方,仍在照耀着,如同它过去,现在,未来所做的那样,并不新鲜地照耀着。
“一杯红茶,一杯牛奶咖啡。”她说。
(完)
女王小说
SM小说
调教小说
成人色情小说
Femdom Novel
Femdom Book
Femdom Story
精彩调教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