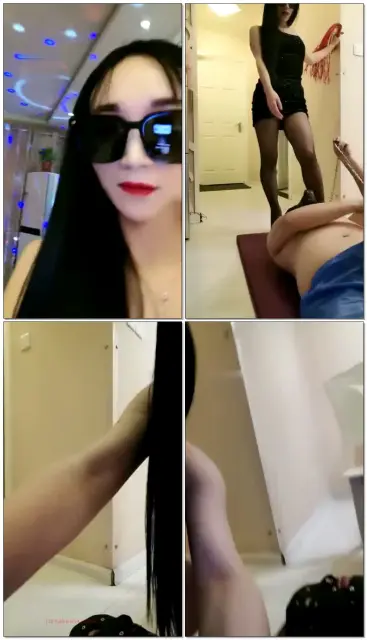最爱的很好
684
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觉得军事基地和电脑电脑电脑的角度讲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间又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祈祷着,只愿求菩提在夕阳下拉长的影子依旧平静。一念花开,一念花落,爱我们的人都已老去,唯剩纺车上的梨花,在朦胧的月光下,那么淡雅、那么素净。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原来,我们都只是遗落在苍茫世海里的一粒尘沙,渺小脆弱,寂寥无言…… 父母,那是上苍在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下的一手牌,我们不能更换,不能丢弃,剩下的就只有去回报。我14岁,她41岁。这是我们生命符号的逆向交集吧,不经意间被时间这个调皮的家伙点染出了巧合的数字。对于孩子,没人用渐渐老去这个词汇;对于成人,更不能用慢慢长大来形容。于是乎,只能这么说,我长大了,而她老了。 小时候她教我背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我咿咿呀呀地学着,乳牙刚掉,说话都漏风,绕口令更是说得一塌糊涂。她却开心地笑,不是大人那种矜持和虚伪的笑,然后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说着绕口令,听我一遍遍努力地把舌头捋直了念。那时,我常傻笑着对什么新鲜的东西都要碰碰摸摸,她也陪我傻笑着摸摸。我知道,她是为了陪伴我。 妈妈有一本日记本,听外婆说这是妈妈怀我时每天的功课。外婆告诉我,妈妈是怕如果她就倒在了手术台上,这本日记本就可以成为我思念她的寄托。我一直很好奇这本日记本里到底写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妈妈把我叫进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把钥匙,她说:“这把钥匙是打开日记本的唯一方式。而这本日记本里,有着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我守了这个秘密十几年,甚至没有告诉过你爸爸,现在我想把十几年的包裹全部都给你。这不是给你施加压力,只是想让你明白,每一样事物的诞生,都是一次黎明与黑暗的交替,你只有战胜黑暗,才能迎来曙光。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一切。”我清晰地记得那个特殊的日子,2009年10月10日——我的十岁生日。那一天,没有什么不寻常的活动,然而因为妈妈的那番话,它会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三生石上。 时至今日,我才愿意把我看到的内容,把那些血淋淋的事实公之于世,这是一个母亲的伟大。“这是来医院待产的第4天,距离医生所说的出生时间还有6天。老公出去买菜了,医生刚才偷偷地走进我的病房,她告诉我,在孩子和健康之间,我必须选择一个。如果孩子出生,即使现在平安无事,到孩子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腰会越来越疼痛,必须终生与药物为伴来克制现在所带来的后果。但如果不要孩子,我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久?医生答应给我三个小时考虑,并且后果只能我一个人承受,不能让家属知道,真的好无助。” 看完这段话,我流泪了,正是这一个线索,才把我这几年一切所不懂的事串在了一起。为什么妈妈做的家务越来越少,为什么每一次在煮完饭之后妈妈会大汗淋漓,为什么妈妈的床头总是有几瓶花花绿绿的药。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就是我这个经常冲妈妈发火,嫌她做的饭太咸,嫌她随意让宠物往外跑,嫌她在我做作业时弄出很大声响的儿子。其实,妈妈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每一次只要我快乐,她就会开心地笑,就像曾经对我笑那样,恍惚间又回到了小时候,和她在地毯上爬着比赛谁先抢到玩具狗时的喜悦;拽着她的手在雪地里追逐宠物的兴奋;在龙庆峡跑着喊她快走的稚嫩。猛然间又倏地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 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她头上的白发……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在思想的蓝天下飞舞,我慌忙地抓住那些回忆的尾巴,怕有一天忘记,怕有一天遗失,怕有一天淡化在时间的边缘,然而这些早已烙在心上,根本用不着追寻。 妈妈,这辈子,我一定用时间来弥补你的伤害,若你安好,若我还在!
女王小说
SM小说
调教小说
成人色情小说
Femdom Novel
Femdom Book
Femdom Story
精彩调教视频